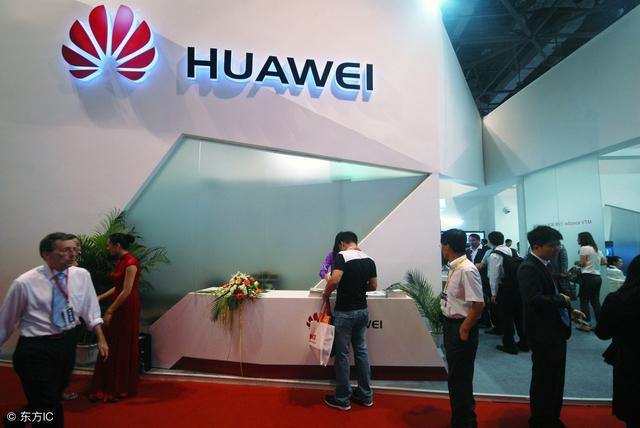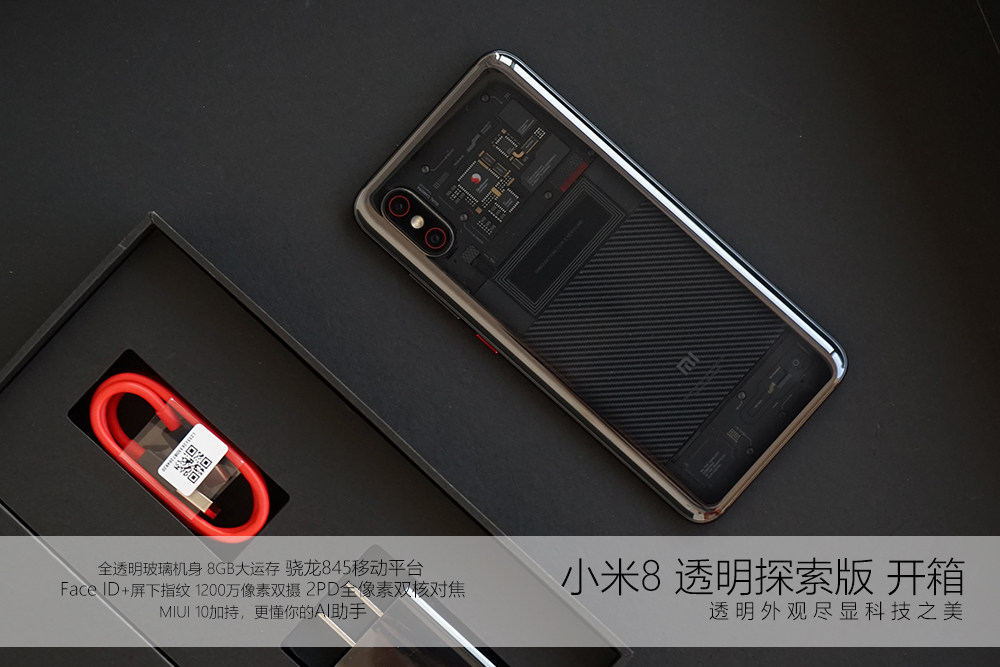Google与Alphabet:能否超越贝尔实验室的宿命
信息时代最有趣的文件之一是11年前发布的、也是 Google 当时 IPO 提交文件的一部分。这份由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签字的文件,既表达了一种对科技创新的深深的激情,也表达了一种对于华尔街的不信任。
佩奇和布林认为,以一种基于信托的责任来平衡风险的做法是有可能的。他们希望实施“一种旨在保护 Google 创新能力的公司结构。”毕竟 Google 不会成为一家为了榨取利润、扩大市场份额而存在的公司——而是希望“开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更多人生活的服务。”佩奇警告说:“作为一个投资者,你们正在下一个可能是有风险的长期赌注,在 Google 团队身上,尤其是谢尔盖和我的身上。”
11年过去,如今的Google,几乎可以任何一种角度来看——利润、增长率、品牌、产品、雇员——都发展得很好,尽管为Google带来巨大财富的产品Adwords 是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还存在争论。但无论如何,Google 已经不再是从前的 Google 了,至少不是 Google 名字代表的那个意思了,现在的 Google 是控股公司 Alphabet 的一部分,也就是 8 月 10 日美国股市收盘后佩奇宣布成立的那家公司。在重组计划中,Google 帝国的盈利业务——Web 搜索和广告,连同 YouTube 和 Google Maps 一起——留在被股票分析师称为“核心 Google”的公司当中。佩奇和布林手中不断扩张的寡头公司,包括人们所知的研发实验室 Google X、刚开始的生命科学和寿命研究,以及家居产品部门 Nest Labs 等等——换句话说,这个庞大帝国所有不赚钱的业务——都会被赋予很高程度的自治权。
你也可以从纯财务的角度来解读这次重组——作为一次务实的举措,为的是让华尔街获得更大的透明度,了解核心 Google 的利润以及陷于一些被揣测中项目的投资,比如 Google X 开发了一款自动驾驶汽车,以及能够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高空气球。佩奇在他关于 Alphabet 的声明中肯定了这种解读的合理性,他强调重组会让公司“更清晰也更负责”。但是在财务原因之外,有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被越来越多地提出,那就是—— Alphabet 是否能够走出一条产业创新的高效发展新路线?
贝尔实验室
作为 AT&T 研发部门成立于 1925 年的贝尔实验室 (Bell Labs) 能够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当时 (1913 年至 1984 年) AT&T 在美国电话服务市场处于垄断地位,也指出了 Alphabet 将会面对的许多挑战。
贝尔实验室发明了许多信息时代的基础性技术,包括晶体管、许多早期的镭射器、通讯卫星以及 UNIX 操作系统。贝尔实验室代表了一家创新型、技术驱动工业组织所能够实现成就的最佳案例。它不仅是美国最顶尖的工业实验室,而且在好几十年里,还是全世界范围内数学、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最精英的研究机构。贝尔实验室还首先实施了声学、半导体和蜂窝通讯的正规化研究。
有相当多贝尔实验室的仰慕者和前员工现在 Google 工作。几乎肯定的是,Google 对于挑战技术边界、长期支持研究项目的意愿,可以说是在当代和贝尔实验室最相似的机构。毕竟 Google 或多或少也是一个垄断巨头,而且其支持研究的资金来源于大众广告业务 AdWords,就像 AT&T 通过出售电话服务来资助全世界最令人关注的物理研究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贝尔实验室的声誉更多靠的是其研究部门的突破性进展,但是不那么耀眼却规模更庞大的开发部门更多承担、完成了贝尔实验室的一次次壮举。约翰?皮尔斯 (John Pierce) 是贝尔实验室的研究经理,他曾经指出该组织的架构反映了一个事实“追求一个想法目标,要花去拥有这个想法 14 倍的努力。”这是皮尔斯几十年经验的真知灼见。基于一项突破性的科学进展打造一个功能性的产品——用晶体管举例——不仅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且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此外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贝尔实验室围绕通讯相关领域来组织研发——这也是获得其母公司 AT&T 的资助唯一合情合理的方式。通讯相关的研发是一个足够广的方向,允许物理化学甚至天文学领域的并行工作。灵活度的空间总是有的,尤其是在数学部门:克劳德?香农 (Claude Shannon) 的信息理论为有效数据传输指明了方向,他在去 MIT 之前有时会整天把时间花费在改进计算机象棋程序和自动化器械上面。但是贝尔实验室的政策太严格,导致 20 世纪最优秀物理学家的离开,约翰?巴丁 (John Bardeen) 是晶体管的联合发明者,他离开贝尔实验室的部分原因是在关于超导性的研究被认为在通讯研究方向上较为边缘,这让他沮丧。类似的情况是否会发生在 Google (或 Alphabet) 令人怀疑。实际上在过去几年里,Google 一直在不断地有意资助昂贵的研发项目,与其核心业务毫不相关,这一点也是佩奇和布林管理时期最令人吃惊的一点。
Alphabet
在过去几十年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在奖励短视、厌恶风险的思考方式,这种情况让曾经拥有知名研究实验室的公司步履蹒跚,比如 IBM 就是如此,而且几乎每一家大型美国科技公司都在远离基础性的、更具野心的应用研究。Google 现在找到了一个使其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大弹性的模式。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 Google 广告业务令人发指的利润率。第二个是佩奇和布林卓越的——也可能有人会说是幼稚的——愿望,想要在有风险的新点子上花钱。
两个人所持有的股份给了他们这样做的权利。但是展望 Alphabet 的未来,倒是值得更精确地定义一下成功意味着什么。看上去 Alphabet 发展更成熟的部分——比如 YouTube 和 Nest,两个恰好都是收购来的——可能最终会成为增长的驱动引擎,加入到 Google 核心广告业务的庞大利润流中去。一些年轻的、以信息为业务导向的公司,Google 也有投资,看起来也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些高利润率的项目。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记住佩奇和布林在对待投资研发项目上很积极,如果他们的一个新想法没有什么利润但是有很大影响 (比如可以用用户数判断,或者是吸引优秀工程师的程度),他们也会用更多的资金投入为这个项目进行补贴。
但是从 Google 宏大的目标来看,想要很快地发明一系列能够显著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创新,这种目标是否能实现到一种最好的程度,让人将信将疑。比如 Alphabet 的延长寿命部门 Calico,人才济济,其目标就说明它是一个疯狂项目 (moon shot),Google X 当中的大部分项目也是如此。此外,研究人类衰老的 Calico 看起来和整个组织并不搭配,除了倚靠 Google 的利润支出以及从佩奇、布林的医学资助中获益这两点之外。
真正的突破
历史表明,围绕某项技术 (比如贝尔实验室的通讯) 组织复杂、创新性的研发力量,能够增加成功的机率,因为开发的专长会更加强科学研究,而制造的专长又反过来促进正在进行中的技术开发。20 世纪工业研究的一个收获就是一家公司的工程、商业甚至销售方面能够为创新进程带来洞察。但是笔者怀疑,我们的目光需要超越 Alphabet,去寻找更新、更专注的工业创新模式。
极富风险的科学技术由 Google 的两位创始人一早埋下了种子,伴随着时间将会发展成为公众所知的一些产品或服务。贝尔实验室即是如此,它的研究为后来英特尔、德州仪器的崛起起到促进作用,甚至包括苹果、微软和 Google 。PARC 也是同样的情况,施乐公司的这家实验室发明了以太网和用户图形界面,但是却没能够将其商业化。但是贝尔实验室先进的科技,在最理想条件下也要花数十年才能商业化,于是未能取保该公司长期的商业成功,尤其是在被判垄断拆分之后竞争环境激烈的情况下。对于想要把赌注下在发明改变世界的科技上来说,贝尔实验室的教训非常现实: 通常将创新的想法进行商业化是难上加难,也更加重要,比产生发明创意更重要。
如果 Alphabet 能够成功实现佩奇和布林的宏大理想,则需要一个个揭开有关创新的谜题,这些谜题让贝尔实验室和 PARC 寿终正寝。 如何针对与核心业务无关的研发进展做商业化?到底是由谁来制造并销售那些无人驾驶汽车?如何从抗衰老研究中打造商业?回答了创新环节的这些问题,将会是创新真正的突破。